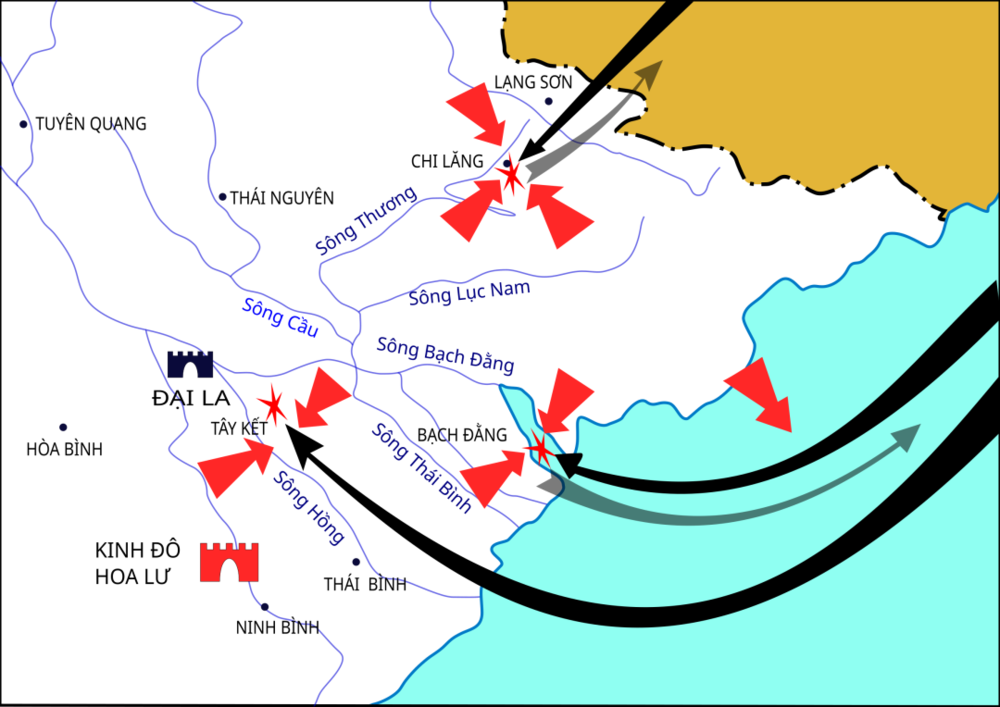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 芥末堆 ,作者:左希,责编:浣熊
他已经连续好几年,反复做同一个梦。
梦里,他坐在驾驶位上,车在夜色中疾驰,没有刹车。他只能不断打方向盘,在城市街巷间兜转、急弯、再急弯。很疯狂,没有尽头。车不会撞,人不会死,但他必须保持清醒,一直开到天亮。
现实中,39岁的李晶也没能停下。创业第五年,他仍在维持三家科创教育机构的运转。为撑住现金流,他先后抵押了自家房产,又动用了父母唯一的住房,前后举债数百万。就像那辆失控的车,一旦发动,只能向前。
“梦有时候是在帮你,”他说,“它替你代谢情绪,缓解那种失控的感觉。”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梦。它更像是这个时代,众多教育创业者共同的潜意识。
01
2025年秋冬,武汉的教培行业冷得沉默。
一些老牌机构开始清仓,有人关闭门店,转战AI托管业务,更多人则悄无声息地离场。家长群里流传着一句话:“谁还在续费谁傻。”课程像今年的柑橘,滞在原地;理念则显得多余。所有人都在问:还能撑多久?
投资人看见“教培”两个字就跳页。地推活动像石子落入死水,不起水花;试听转化率持续走低,家长的到访热度就像冬天的水壶,刚冒几缕白气便凉了。
李晶的三家校区,在册人数三年来首次停滞。事实上,自创业以来,危机便如影随形。时间一长,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入了一种长期的应激状态,“会更多地释放恐惧、不断预演最坏的情况”。于是,他开始拍视频。为了迈出这一步,INFP人格的李晶做了漫长的心理建设。“你相信自己会赢,但万一不是呢?那种补偿心态其实非常恐怖”。
那天晚上,他喝了半斤白酒、一升半精酿,只为压住脑子里“哪句话该讲、哪句话不该讲”的念头,“单凭直觉来”。他坐在仓库角落,对着镜头讲了四个小时,中途卡壳、走神、重录,直到凌晨。同事陪着他拍,又喊来朋友助阵。他怕一个人呆着。
“这次做IP不能失败。”他说,“它是我手上为数不多的杠杆。”他的微信里有4000多个好友,有家长、同行、大学同学、曾经的客户。他知道,只要这次失败(不是播放低,而是没人回应),他最后一层“社交信用”也会被透支完。
剪出来的成片只有三分钟,标题是朋友起的,带着股狠劲:“87年,辞掉铁饭碗,为了做教育倾家荡产,他经历了什么?”
2025年12月3日,视频发布。当晚播放量迅速破十万,第二天跨过五十万,教育圈率先刷屏。评论区里,有人说“终于有人敢讲实话了”,有人提起他疫情期间四处奔走帮忙找物资,说:“这才是武汉人。”
他没有细读评论,但每条都点了“谢谢”。前后点了15000个。
本地家长陆续走进校区。最初是带着试探:“视频里那个人,真的在上课吗?”试听预约随之爆满,转化率飙升。他连夜搭建承接流程,重新设计话术、优化接待动线、培训前台老师。一边拍视频,一边上课,一边调流程。
流量来了。他没有去判断自己是否“红了”,很少打开后台的涨粉曲线。直到后来,学生在专业赛事中斩获冠军,视频再次出圈,情况才逐渐明朗。
视频出圈后,月签新生的数量翻了五番。白天校区事务缠身,晚上回家刷留言,一边看一边睡着,凌晨三点惊醒后接着刷,一直看到天亮,再洗把脸,进教室。
02
2020年1月1日,李晶的第一家科创教育中心在武汉开业。门店选在城区房价最贵的购物中心,租金高,但人流量集中。他希望先跑通一个“课程结构—工程路径—交付模型”的原型,再谈复制。那时他刚离开体制不久,人还带着惯性。他说自己并不急着赚钱,更想先把一件事“做立住”。
22天后,武汉封城。城市被按下暂停键。机构停课,员工回家,房租照交。他在空荡荡的校区里怅然,第一次意识到:创业并不等于掌控。
八个月后复课。没有刻意营销,却迎来一波报名。孩子在家憋得太久,家长需要出口。他顺势开出第二家校区,选在经开区永旺商圈。租金更高,但他当时相信,这是窗口期。“后来才知道,那可能是行业最后一次窗口。”他说。
2021年,“双减”落地。虽然监管重点并不在素质教育,但支付意愿开始下滑。家长变得犹豫,“再看看”“先缓缓”成了常用回复。他没有降价,把精力放在课程内容和教务服务上,想用产品力站住脚。但人流一断,再好的课也难以转化。
2022年,疫情反复。武汉一年内经历六次封控,三家校区轮番关停、复课。排课表常在凌晨改好,早上又被推翻。退费申请和投诉电话堆在前台。他说,“那时校区像战场,老师像急救员。”
当年亏损280万。年底,公司账面现金流只够支撑三个月。他第一次抵押房产,从银行贷出92万元,用来填补周转缺口。
2023年,一笔此前被忽略的合规成本被重新计入,需要一次性补齐,金额接近50万元。公司已无法再拆借,他只能动用家庭资源。他瞒下所有人,以“公司贷款需要担保”为由做了亲子公证,抵押了父母唯一一套住房,换来69.5万元。手续办得很快,他却不敢多看合同。“我怕看清楚,就签不下去了。”
钱到账后,他拆成几份。工资、房租、物料、供应商,一笔一笔摊开。他说,工程出身的人,即便在亏,也要亏得有条理。
这五年里,他并非没想过停下。只是停下的代价更高。教育不是一般生意。背后是几百组家庭、几十名员工。一旦停摆,问题不会慢慢消失,只会集中爆发。他把公司形容成一台“带电机器”:只要通着电,就有课程、有交付、有纠纷;一旦拔掉电源,反而崩得更快。
很多时候,他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根随时会塌的平衡木上,不能腾挪,因为下面是冷硬的水泥。只能立正站好,脚趾抠紧,撑一天算一天。
每个月,他会在一张A4纸上手写现金流。水电费、耗材、空调、清洁频次,一项项抠。这五年像一个黑洞,吞掉了原本所有关于规划的想象。“车没刹住,但也没撞。”
03
他越来越像一个精密仪表下的操作工,每一步都踩在信用系统的边缘。
2020年之后,为了维持三家校区的现金流,他陆续开通了十几个账户:微粒贷、借呗、360借条、企业周转贷、税贷、信用卡分期。每到月中,他就要开始“打表”,哪一笔到期,哪一笔可续,哪一笔能拆东补西,哪一笔再拖三天就会逾期。他说,这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手工对冲。
员工工资不能延,家长退费不能拖,课时交付不能断。这些“信用锚点”一旦松动,机构就会从运营问题迅速滑向声誉危机。最初几年,这套调度还能运转。平台给额度,系统给续期,只要按时还款,链条就能接上。但到了2025年,这种默契突然失效。很多原本可以续贷的平台,在后台直接标红,系统自动关停。
这种静默的断链,比明确的拒贷更让人慌张。他意识到,作为一名被外界不断评估的创业者,已被征信评分、账户使用率、行业标签、地区分布等被系统标注的数据折叠进看不见的算法里。
他笑说:“如果征信真‘花’了,那也得活。”也是在这种状态下,他接到了那通诈骗电话。
2025年2月,武汉刚回暖。他有一笔36万元的循环贷款到期。电话那头自称是银行客服,说可以协助延期,只需配合一套线上验证流程。
“我当时像个失智的老年人。”他说,“对方说什么我就照做,连验证码都没想清楚就点了。”对方诱导他开启屏幕共享,完成了一次人脸识别授权。等他回过神,一笔来自境外机构的高息贷款已经生效,年利率23%。
他立刻报警。但所有操作都由他本人完成,警方无能为力。“不是贪心,”他说,“是太怕断气。现金流一断,整家校区就停摆。”
2025年10月,一个老朋友,也是银行从业者,打来电话,说刚好有一笔额度可以用。“我把这几年的流水、负债、课时结构,甚至员工层级和各分校的营收比例一股脑地倾诉给他,整个人都在发抖,像是对着陌生人解剖自己。”这些年,他一直在朋友圈维持着“正能量”,所有负面情绪都默默消化。最终,他成功拿到了150万贷款,年利率3.1%。
钱到账那天晚上,他睡着了,没有做梦。很久没有这样了。
04
2009年,李晶进入体制。
那一年,职业教育进入政策的“快车道”。政策密集出台,地方政府推动产教融合,学校鼓励项目制教学和企业合作。他所在的学校,是中德合作试点项目落地单位之一。汽车电子机械专业被列为重点试点,他刚入职,就被推到课改一线。
他并不抗拒这些工作。相反,那些年,他感到一种少见的确定感。他主导“3+2”中高职贯通项目,修订课程标准,搭建人才培养方案,跑企业、建实训基地。两个暑假,他几乎没离开过办公室,白天改方案,晚上对表格。
“那时候真觉得,事情是往前走的。”他说。他是教材主编,是赛事指导老师,是团委干部,是体制内典型的“青年骨干”。工作强度高,但回报路径清晰,干得多,升得快。更重要的是,他相信自己在做“有用的事”。
那几年,整个社会也在奖励这种信念。地方政府需要职业教育承接产业升级,学校需要年轻教师推动改革,企业愿意参与培养方案共建。教育不仅是育人,也是就业通道,是城市发展的配套系统。
但这种感觉,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慢慢地,他发现,文件越来越多,会议越来越密,考核指标层层叠加,真正落到课堂与学生身上的内容,反而被不断挤压。一套课程是否有效,变得不如是否“可汇报”;一次教学改革是否成功,取决于有没有形成“成果材料”。“有时候你会不知道,这些文件是写给谁看的。”他说。
与此同时,体制外的世界开始变得喧闹。凭借专业背景和项目经验,他接触到企业培训和咨询项目。一次短期合作的收入,抵得上几个月的工资。
2015年,一次大学同学聚会。一桌二十人,几乎全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汽车工程师。有人换房,有人升职,有人跳槽。他是唯一的老师,也是收入最低的那一个。
2017年,他选择离开体制。
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赚钱。但在他看来,更深的原因在于一种结构性的转向:体制内,责任是被分摊的;体制外,责任则需要主动承担。当组织的信任成本迅速上升,责任的承担变得更加复杂和高风险。
这种变化,在创业初期并不显现。2019年,他创办科创教育机构时,仍能找到愿意并肩的伙伴,愿意长期值守的老师,愿意耐心等待结果的家长。那时,大家还相信“共同体”:相信只要事情做得对,时间会给答案。
2021年之后,这种信念开始瓦解。疫情、政策、市场的压力交织,关系的成本被重新计算。投资者转向观望,合作伙伴寻求自保,家长的耐心也在迅速消耗。在这种时刻,自救的神话开始蔓延,每个人都在告诉自己,能撑下去就是成功。
灾难,不再是某个即将来临的突发事件,而是一种被无限延续下去的生活。成功被当作一种道德能力:对抗自己的脆弱、对抗这个迅速脱离共同体的世界。
05
到2024年前后,李晶开始明显感觉到,团队正在进入一种不同于创业初期的状态。
会议照常召开,课程照常推进,制度也没有出现明显松动,但一种无需言明的疲惫在内部蔓延开来。有人不再主动发言,有人只是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,偶尔有同事不见了,不再告别,留下空空的座位。有人在社交平台发文,讽刺这个行业的“自我感动”。而他依旧每月在那张白板上写下新一轮教学排班,像是在为一支正在消散的队伍继续演练。
那是一种逐渐被淡化的存在感。每个人低头埋头完成自己的部分,彼此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,原先的热忱与共同体感慢慢消退。
创业初期是什么状态?那时是讲愿景、发工资,每个人还能想象未来;现在,靠的是“这事不能散”“孩子还在”等一种近乎道德绑定的牵连。不能扩张,也不敢收场。
“教培是一个情绪过载的行业。”他说,“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一线老师身上,家长的焦虑,孩子的表现,课堂的反馈,还有投诉电话。”这些年,他学会了如何成为团队的缓冲区。他笑称自己是“情绪工程师”。家长的投诉,他先接住;老师的疲惫,他先消化;学生的情绪,他先安抚。
有一段时间,他会下意识地挽留那些显露出犹豫的人。也是在那段时间,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:维持本身,也可能是一种伤害。后来,他不再劝人留下。他开始理解那些选择离开的人。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去处,而是已经在心里,提前结束了这段关系。
他也尝试过修复。聚餐、团建、谈话,但效果有限。“人心不是靠几顿饭就能留住的。”他说。后来,他不再强行拉着团队向前,而是默默替每个人多做一点事:为留下的老师分摊课程,把家长的情绪劝解扛在前面,替人垫付一些零散费用,从不多解释。
他逐渐意识到,公司不是家,它只是装过一群人一段时间的生活。“情绪银行”是他给这种关系起的名字。他知道,这个账户里的余额已经不多,随时可能透支。
“像水里的一片叶子,”他说,“先别沉。”
06
回头看这五年,李晶发现,自己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“未来”。每个人似乎都被困在看不到尽头的时间深井中。
时间被切得很碎。以天为单位处理事务,以月为单位偿还债务,以季度为单位做计划。至于更远的事,很少再去想。“未来这个词,对很多人是一种奢侈。”他说。
在长期的应激状态里,人很难再谈延展。更多时候,未来只是一个倒计时。什么时候钱会断,什么时候团队会再走一个人,什么时候系统会给出下一个“不可抗力”。
直到2024年底,他尝试把时间重新拉长一点。他开始重新设计一门AI编程课程。课程的起点不再是知识点,而是问题本身:“这个世界,还有没有机器无法替代的事情?”课程里,他不急着教算法,而是让孩子先提出问题:如何让一台机器理解人的情绪?如何让技术参与照料,而不是只追求效率?孩子们要先观察、记录,再尝试用代码去回应现实。
“很多课程,其实是在用旧地图找新大陆。”他说,“但AI真正逼迫我们的,是重新思考为什么要学。”他更愿意用“载体”这个词来形容教育。在他的理解里,教育不是目标,而是一个载体:连接技术与人、连接乡土与世界、连接孩子和他们自己。
即便是看似最热门的桌面游戏设计、图像识别课程,他也会刻意放慢节奏,加入一些“非效率”的任务:让孩子回家观察老人三天的行动路径,尝试设计辅助系统;让他们画出理想教室的样子,再用工具把它变成草图。“你不能只教他们适应未来,”他说,“还得让他们有机会想象未来。”
在李晶看来,“未来”不像一个即将到来的外部时间,更像一个需要在当下建构的内部世界。
家长更关心“有没有用”,老师不太敢讲真话,机构之间也越来越谨慎。慢、试错、等待,这些词在现实中逐渐失去耐心。
可即便如此,他仍然记得一堂课上,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问他:“老师,什么叫自己想出来的?”那一刻,他意识到,哪怕在系统高度疲惫的今天,仍然有人在追问一些“不合时宜”的问题。
“教育最动人的地方,不是给答案,”他说,“而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,让人可以安心提问。”他知道,这样的空间越来越稀缺,但他仍然想继续搭建。“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听,我也想把这件事讲完。”他说,“讲一个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。”
他偶尔还是会梦见那辆没有刹车的车。夜色、急弯、灯影模糊。车不会撞,人也不会死,但始终不能闭眼。
“我们这一代人,可能一生都在处理一件事,”他说,“速度取代了意义。”但教育不能放弃意义。哪怕慢,哪怕痛,它仍然要留下那个问题:我们究竟想把孩子带向哪里?
车还在夜里疾驰。只是这一次,他开始试着松一点手,让速度之外的东西得以显现。
后记:
新年,李晶送给自己一条无屏幕的手环。充一次电,可以用一个月,能记录睡眠、心率和步数。他说自己最近总觉得没睡好,但偶尔瞥一眼数据,发现并不糟,心里就会安定一些。
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之中。人们最关心的,只有两件事:资金是否安全,教学是否可靠。如此,坦诚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事情。在一切都需要迅速反应的丛林中,强大几乎成了一种必须被展示的状态。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不断地“讲成功”来维持信心,现实本身,已经很难再被当作安抚人心的来源。
人们习惯用“个人选择”解释一切,却忽略了一个事实:许多所谓的选择,不过是被动接受的路径。时代首先改变的,往往不是命运,而是人对时间的感知。个体并不总是站在决定的起点。
后来有一次户外探险,李晶在完全黑暗的溶洞里连续走了十二个小时。没有参照物,也看不清前方,每一步只能跟着脚下的感觉往前挪。他意识到,在长时间的黑暗里,人很容易失去对“方向”的判断,只能靠不断挪动,来确认自己仍在途中。
卡尔维诺说:“在崩塌的世界中,不被吞噬的方式,是去建造。”在现实中,这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、更少的保护,以及更多误解。
事实上,当时代的飓风刮起,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无感:教育这部机器仍在运转,但越来越多的人,不再相信机器之外还有意义。车不停,并非为了抵达,而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停车。